内容详情
2025年09月10日
梨园书声,师恩如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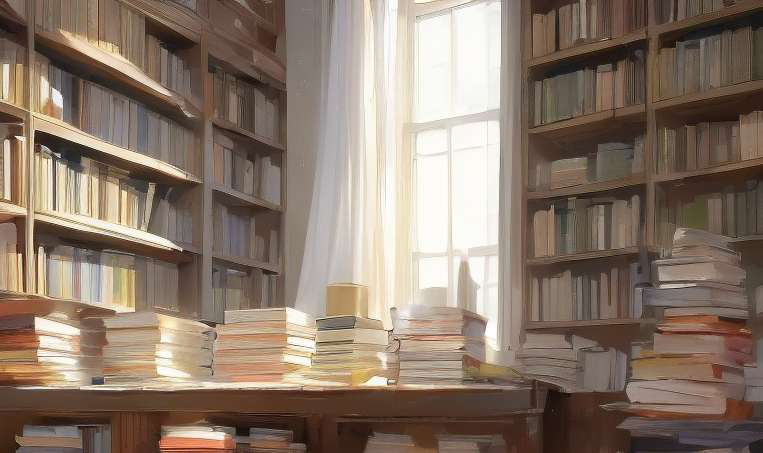
编者按 一方书桌,三寸粉笔,一生光阴,四季流转。教师是青春梦想的奠基人,是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。9月10日是我国第41个教师节,本报推出“特别策划”,刊发一组与教师节主题相关的稿件,向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,祝每一名人民教师,节日快乐!
郝贵良
20世纪80年代,我就读于赣东一所乡村初中。学校坐落在山崖上,背后有一片广阔的梨园。在那里,我遇见了影响我一生的语文老师——黄福龙。
黄老师脸型方正,颧骨略高,眼睛明亮有神。他平时话不多,身上总带着一种沉静的书卷气。看得出来,他读过很多书,眼里常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,像是藏着许多还没讲完的故事。
春天,几场雨过后,梨园里的花就悄悄开了。那些老梨树枝头堆满洁白的花朵,远远望去,像落了一层薄雪。黄老师那时正在读函授大学,常常早起,站在矮墙外的梨树下读书。有一天清晨,他正大声读着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当他读到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”的时候,一阵微风拂过,梨花纷纷飘落,洒在他的头发、肩膀和脚边。那一刻,他仿佛披上了一身的花瓣,安静地站在晨曦中。那个画面,我至今难忘。
受黄老师的影响,我们也开始早早起床,走进梨园读书。有人背英语单词,有人读政治题,也有人模仿黄老师朗诵古诗。梨花开得正好,静静地听着少年的书声。天刚蒙蒙亮,霞光洒在梨花上,也照着我们手中的书本。那时的梨园,不只是一片果园,更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读书堂。
黄老师讲课很好听。他声音洪亮,又亲切自然,像春风一样温暖。我记得他讲岑参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,读到最后那句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时,他的眼神变得特别温柔,脸上带着笑意。那一刻,我们真的好像看见了窗外那一片梨花如雪的场景。就是从那时起,我开始喜欢上了诗,喜欢上了语文。
黄老师住在一间很小的宿舍里,紧挨着梨园。屋里除了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、一个毛巾架和一只水桶,就没什么别的东西了。虽然简陋,但却是我最爱去的地方。因为他那里有书——有《边城》《红楼梦》,有函授教材,还订了《诗刊》《辽宁青年》这些杂志。怕我们看得入迷,耽误其他功课,他常把杂志藏在床单下面。
但我还是发现了。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和崇拜,我常悄悄去翻看,尤其是《辽宁青年》,里面有很多励志故事和格言,我常常边读边抄,有的还背下来。这些阅读让我的作文越写越好,每到作文课,我就特别期待。黄老师常拿我的作文当范文念给大家听,他读得有声有色,让我心里特别温暖。也就是在那时,我悄悄萌生了一个念头:将来,我也要当语文老师。
初秋的一天,同桌跑过来告诉我:“你的文章和黄老师的诗一起‘发表’啦!”——原来都被抄在了教室后面的黑板上。我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,那天中午,我用饭票请同桌吃了个肉包子。
黄老师对我们特别用心。那时候大家都没钱买课外书,他就自己买书、挑题,亲手刻钢板、油印试卷。常常看到他在梨树下推着油印辊子,手上沾满了墨。他却不在意,随手摘几片梨树叶搓一搓,对我们笑笑。每一张试卷,都是他的心血。我们也特别珍惜,认真做题,努力考好。
他常常鼓励我们说:“山外有山,你们要走出这片梨园,去看更远的世界。”所以我们都很用功。学校每晚十点熄灯,熄灯后最早点起煤油灯的,总是黄老师的窗口。借着那点橘黄色的光,我常去他宿舍问问题、借书,有时只是喝一口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。那感觉,像是去了一位大哥家。
我们也学着他,自制煤油灯——用墨水瓶、牙膏皮和棉线做成灯芯。夜晚,一盏盏小灯在教室里亮起,窗外的梨园静悄悄的,只有黄老师查夜的脚步声。灯光摇曳,照亮的是我们想靠读书走出大山的愿望。有一次,同桌不小心打翻煤油灯,油全洒在我本子上。交作业时我很忐忑,黄老师却开玩笑说:“这作业‘辣眼睛’,但有味道!”
夜读结束回到宿舍,常常已是深夜。冬天夜里冷,偶尔有人躲在被窝里说话。黄老师来查寝时总是先静静站在窗外,然后轻轻咳嗽一声,说:“还不睡?再吵就请你们去梨园晒月亮!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。他会在门外站一会儿,确认我们都睡了,才轻轻离开。
那年中考,我们班取得了优异成绩:近三分之一同学考取中专、师范,还有同学夺得全县第一。这所梨园深处的学校因此赢得了“小临川”的美誉。黄老师后来被提拔为教导主任、副校长、校长。而我因英语偏科,以6分之差与师范失之交臂,进入了县里最好的高中。
但黄老师点燃的那盏灯,从未熄灭。他带我走进文学,让我从此一生爱书。如今回头再看,那片梨园、那些晨读与夜灯、那位站在花雨中的老师,依然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。
 苏公网安备 32061202001248号
备案/许可证号:苏ICP备11084708号-2
苏公网安备 32061202001248号
备案/许可证号:苏ICP备11084708号-2

